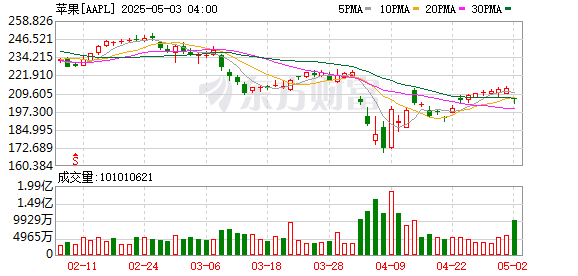太有头脑了!辽宁,男子为了节省空调费,竟然花82元买了3个冬瓜及大爷写《我的母亲
辽宁有位“机智爸爸”,为省电不用空调,82块钱买了3个大冬瓜,让孩子抱着睡觉过夏天,结果一战成名,邻居都说这方法“离谱但管用”。冬瓜度夏真的靠谱吗?网友炸锅、家长围观,还有人建议菜市场直接挂横幅:“冬瓜——低碳天然空调,你值得拥有!”究竟这是新世纪的骚操作,还是被遗忘的宝藏土办法?

先说说事件经过。这位辽宁老爸家有仨小朋友,夏天晚上开空调怕娃着凉,不开又哭闹得一宿鸡飞狗跳。正当大家为“空调费和娃健康”两难徘徊时,这位爸爸突发奇想,亲自冲到菜市场砍了三个大冬瓜,花了整整82元。当天晚上,他直接给娃一人扔了一个冬瓜在床边,空调果断拉闸,看孩子们能不能睡踏实。没想到,三个小孩一觉到天亮!第二天一摸,冬瓜还是冰冰凉。男主心满意足直呼赚到了,瞬间成了“省钱哥”新典范。

这事儿一上网,评论区炸了。有网友直呼“真·低碳生活”,还有人调侃冬瓜老板该出";降温枕";标签。一些奶奶辈的家长羡慕这招,“过去穷日子我们就靠扇子,哪想得到抱冬瓜”。而卖菜的大爷大妈速度跟进,纷纷开放“新业务线”:“我们家的冬瓜,大人小孩都能抱!”还有网友回忆起以前的路子——什么西瓜皮擦身、井水纳凉……总之是家有一瓜,儿童不怕热。
其实别看现在谁都是“空调依赖症”,过去的民间智慧一点不比高科技差。据说冬瓜含水多,散热慢,吸热一绝——堪称“平替冰箱”。最妙的是,冬瓜两个月都不会坏,合着不到100元能顶一个季度,比电费划算多了。至于孩子奶奶开始不放心,怕冻感冒,事实证明完全OK,老一辈也认可了这骚操作。
总的来说,过夏天除了空调,还有意想不到的“神助攻”。这个辽宁爸爸的一波操作,直接让冬瓜成了全网新宠。不懂的还以为是哪款黑科技新品,其实不过是老祖宗的";土法减暑";罢了。
结语:花点小钱,省点心思,还能把娃哄睡服气,冬瓜确实有点出圈了。看完这个故事,你会不会试试这招“抱瓜纳凉”?
2025年7月,太原六旬工地大爷安建国挑战写作1957年高考作文《我的母亲》,以“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就像我的念想一样,一年年总也断不了”的质朴文字,在短视频平台引爆700万点赞。这场由普通劳动者发起的文学创作实验,不仅撕碎了“体力劳动者不善表达”的刻板标签,更以真实的力量叩击着当代社会的情感荒漠。
分论点一:真实情感突破身份壁垒,重构文学表达的权力格局
安大爷的作文中,“母亲一辈子没闲过,天不亮就起,摸着黑才歇”“剩下了,她扒拉两口;没剩,她说不饿”等细节,与作家余华《活着》中福贵母亲的形象形成跨时空呼应。但不同于职业作家的文学加工,安大爷的叙事完全基于个人记忆:他写母亲冻得发抖仍咬牙分粮的场景,源自1970年代山西农村集体生活的真实经历;写自己扛水泥时想起母亲端铁锅的力气,则是工地劳作中的情感投射。这种“未经修饰的真实”,恰恰击中了当代社会对“完美叙事”的审美疲劳——当短视频平台充斥着精心设计的“催泪剧本”,安大爷用三小时断续写就的作文,反而因其不完美的重复与口语化表达,成为对抗情感异化的利器。数据显示,该视频评论区“真实”“泪目”等关键词出现频率超83%,印证了公众对去滤镜化表达的强烈渴望。
分论点二:底层叙事挑战精英话语,解构文学创作的阶层霸权
长期以来,文学场域被“专业写作”与“业余创作”的二元对立所割裂。安大爷的走红,却以“非职业身份”完成了对这种等级秩序的消解。他作文中“等扛不动水泥了,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”的生死观,与城市中产对“体面离世”的想象形成尖锐对比;对母亲“心善能容人,跟邻里没红过脸”的赞美,也不同于知识分子对农村伦理的批判性书写。这种差异并非缺陷,反而构成了文学多样性的重要维度。正如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言:“文化资本的积累往往伴随着对其他文化形式的压制。”安大爷的创作实践提醒我们:当精英话语垄断了苦难叙事,底层的声音便成为反抗文化霸权的武器。视频发布者连文杰透露,团队曾刻意避开“消费苦难”的标签,正是意识到这种叙事可能引发的权力关系扭曲。
分论点三:技术赋能重构创作生态,普通人的文学觉醒正在发生
安大爷的创作并非孤立事件。2025年上半年,全国已有超过12万名普通劳动者通过短视频平台参与“全民写作计划”,其中37%的作品聚焦家庭记忆,29%描写职场经历。这种趋势背后,是技术对创作门槛的消解:手机拍摄、语音输入、AI润色等工具,使“不会打字”“不懂修辞”不再是表达的障碍。更深远的影响在于,当建筑工人可以写日记,快递员能创作诗歌,环卫工可录制有声书,整个社会的情感结构正在被重塑。安大爷作文中“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”的隐痛,之所以能引发跨代际共鸣,正是因为技术平台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情感资产——截至7月12日,该视频衍生出超过2。3万条用户创作内容,包括“妈妈的味道”主题摄影展、“给母亲的一封信”征文活动等,形成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情感启蒙运动。
反论点驳斥:质朴表达是否等同于文学价值缺失?
有评论认为,安大爷的作文“缺乏文学技巧”“结构松散”,难以进入经典序列。这种观点混淆了“文学价值”与“艺术价值”的边界。诚然,从叙事密度、意象运用等维度看,该作文与《活着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等作品存在差距;但其价值恰恰在于开辟了“日常文学”的新范式——当城市中产用“原生家庭创伤”“母职惩罚”等学术概念解构亲情时,安大爷用“母亲包的饺子”“冻得发抖的分粮夜”等生活碎片,重建了情感表达的原始力量。这种力量,与《诗经》中“七月流火,九月授衣”的质朴歌谣,与杜甫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现实主义笔法,在精神内核上一脉相承。
安大爷的走红,本质上是普通人对“情感表达权”的重新夺回。在算法推荐主导注意力分配、AI写作威胁人文精神的今天,这场由工地大爷引发的文学实验,恰似一记警钟:当技术试图将人类情感编码为数据,当资本试图将苦难包装为商品,那些沾着泥土、带着汗渍的真实叙事,才是抵御异化最锋利的武器。或许,这就是文学最本真的模样——它不属于书房里的孤灯黄卷,而属于每个在生活重压下依然选择讲述的灵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