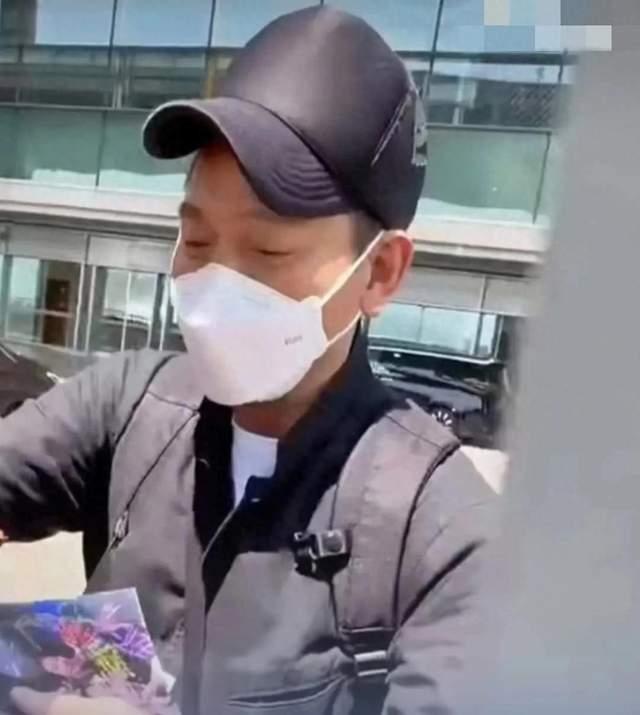男子1块7买过期饮料获赔1000元 ,理发店给男子灌肠涉嫌犯罪-北京交通流量已经
男子1块7买过期饮料获赔1000元。
热。
2024年12月,广西桂林男子秦某以1。73元购买贴有“折扣商品”标签的过期饮料,因超市用标签遮蔽生产日期与保质期信息,最终获退货款并获赔1000元。这起看似“小题大做”的诉讼,实则撕开了食品经营领域“标签套路”与“法律盲区”的双重遮羞布,折射出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市场监管的深层博弈。
分论点一:标签遮蔽行为突破法律底线,构成“恶意误导”?。
超市在过期饮料上张贴“折扣商品”标签,不仅覆盖了法定强制标注的生产日期与保质期信息,更在标签上标注“打印日:2024/12/10,25/01/10”等模糊信息,试图通过技术性手段掩盖商品过期事实。根据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,禁止生产经营“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”,而超市的行为已同时触犯“虚假标注”与“销售过期食品”双重禁令。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,超市“遮蔽保质期标识并标注误导性日期”的行为,足以使普通消费者对商品实际状态产生错误认知,构成法律意义上的“明知故犯”。这一判决与2024年江苏京口法院审理的同类案件形成呼应——某超市因用“买一赠一”标签遮蔽过期食品生产日期,被判赔偿消费者800元,凸显司法对标签欺诈的零容忍态度。
分论点二:千元赔偿不是“过度维权”,而是法律赋予的“惩罚性武器”。
超市辩称“秦某未饮用饮料,未造成实际损害”,试图将“食品安全标准”简化为“人身损害结果”。然而,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四十八条明确规定,经营者销售“明知不符合安全标准”的食品,消费者有权主张“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”的赔偿,且“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计算”。这一条款的核心逻辑在于,通过惩罚性赔偿倒逼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,而非仅补偿个体损失。数据显示,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食品安全民事纠纷中,78。3%的案件适用千元最低赔偿标准,其中62%的涉案商品价值低于50元。正如最高法法官在2024年食品安全司法解释解读中所言:“小额食品的‘低成本违法’现象,必须通过‘高代价赔偿’打破。”?。
反论点:职业打假人滥用诉权,消耗司法资源。
部分观点认为,秦某“明知商品过期仍购买”的行为属于职业打假,其动机是获取赔偿而非维护权益,应限制其诉权。但司法实践早已突破这一争议:2024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三条明确规定,“因食品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,购买者向生产者、销售者主张权利,生产者、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,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”。这一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,食品安全关乎公共利益,即使消费者存在“知假买假”行为,其监督权仍受法律保护。更何况,秦某的举证行为(保留购物小票、拍摄标签照片、提交商品实物)完全符合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能力范围,与职业打假人的“批量采购、专业化取证”存在本质区别。
驳论:强化经营者责任不等于加重企业负担?。
有企业主张,千元赔偿标准“过于严苛”,可能迫使小微经营者因“一次疏忽”而破产。但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4年的调研数据显示,在适用千元赔偿的案件中,92%的经营者因首次违规被处罚后,均建立了食品保质期预警机制,未再发生同类问题。反观涉案超市,其库存管理系统显示,案发前3个月内已有5批次商品因标签遮蔽被投诉,但企业未采取任何整改措施。这表明,惩罚性赔偿的真正价值不在于“罚没收入”,而在于推动经营者从“被动应付检查”转向“主动防控风险”。例如,上海某连锁超市在引入AI保质期识别系统后,过期商品投诉率下降89%,而系统投入成本仅相当于3起千元赔偿案件的支出。
从1。73元到1000元,这起案件的赔偿金额差异,恰恰体现了法律对食品安全“零风险”的追求。当经营者试图用“折扣标签”掩盖过期事实,当“最佳食用期”的辩解成为逃避责任的遮羞布,司法判决用最直接的方式宣告:在食品安全领域,任何技术性欺诈都逃不过法律的眼睛,任何侥幸心理都将付出沉重代价。对于消费者而言,这不仅是维权胜利的示范,更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——保留证据、依法主张,每个人都能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;而对于经营者,则是警示:唯有敬畏法律、尊重生命,才能在市场中行稳致远。
理发店给男子灌肠涉嫌犯罪?。
合肥一男子在理发店两年充值430万元接受灌肠、针刺排毒服务后健康受损,退费遭拒的事件,不仅撕开了生活美容行业非法行医的灰色幕布,更暴露出预付卡监管、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伪科学营销的三重危机。这起看似荒诞的消费纠纷,实则是资本逐利与监管滞后碰撞下的典型样本,折射出社会治理中亟待填补的制度漏洞。
立论点:非法行医与预付卡失控的双重失范,构成对公共健康与市场秩序的双重威胁。涉事理发店工商登记范围仅为“理发服务”,却擅自开展灌肠、针刺排毒等侵入性医疗操作,其行为违反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中“非医疗机构不得开展诊疗活动”的强制性规定。更触目惊心的是,该店单次充值高达38。8万元,远超商务部规定的单次预付卡充值上限5000元,且资金缺乏第三方存管,导致消费者退款无门。这种“超范围经营+预付卡失控”的组合,使行业风险呈几何级数放大。
分论点一:非法行医的刑事风险远超民事赔偿,需以“零容忍”态度划清法律红线。灌肠、针刺排毒属侵入性医疗行为,操作不当可致肠穿孔、感染性休克甚至死亡。2024年上海某瑜伽馆非法灌肠致幼儿住院的案例,已为行业敲响警钟。本案中,涉事门店既无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,操作人员亦无医师资格,若经鉴定造成消费者轻伤以上后果,将触犯《刑法》第336条非法行医罪,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;若存在虚构疗效、诱导消费等欺诈行为,且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,则可能构成诈骗罪,430万元金额已达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标准,最高可判无期徒刑。法律必须亮明“非法行医即犯罪”的底线,避免将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行为降格为行政处罚。
分论点二:预付卡监管缺位催生“资金黑洞”,需建立全链条防控机制。程先生卡内170万元余额难以追回,暴露出预付卡资金监管的致命漏洞。商务部虽规定单次充值上限,但缺乏强制执行手段;市场监管部门对超范围经营仅能罚款吊销执照,难以追回已消费资金;金融机构未介入预付卡资金托管,导致商家可随意挪用。对比英国《消费者权益法案》要求预付卡发行方必须将资金存入独立信托账户,我国需建立“备案-存管-保险”三重保障:强制商家在商务部门备案预付卡信息,要求金融机构托管资金并定期公示流向,同时引入预付卡保险制度,对商家跑路进行兜底赔偿。
反论点:消费者应承担部分责任,过度消费属个人选择。部分观点认为,两年充值430万元超出普通消费范畴,消费者应具备基本判断力。然而,这种“受害者有罪论”忽视了商家系统性诱导的恶劣性。涉事门店采用“跪地哭穷”“业绩养家”等情感绑架话术,利用消费者的同情心与社交压力实施操控,已构成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中的“欺诈性销售”。此外,商家宣称灌肠可“减肥”“恢复年轻状态”等伪科学话术,精准狙击中老年群体对健康的焦虑,本质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精神控制。监管部门需明确:当商家采用非法手段诱导消费时,消费者责任应被大幅减轻。
驳论:行业自律不能替代法律规制,需构建“穿透式”监管体系。有声音呼吁加强行业自律,但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的界限模糊,使自律沦为空谈。涉事门店将灌肠包装为“肠道SPA”,将针刺美化为“经络疏通”,正是利用概念混淆逃避监管。破解这一困局需三管齐下:其一,卫健部门应发布《生活美容服务负面清单》,明确禁止灌肠、针刺、注射等医疗行为;其二,市场监管部门建立“预付卡消费信用评级”,对违规商家实施“一票否决”;其三,推广“消费维权证据固化”平台,要求商家强制留存服务全程录像,为纠纷举证提供依据。
从合肥到全国,这起事件揭示的不仅是某家理发店的违法问题,更是整个生活美容行业的系统性危机。当“伪医疗”披上“养生”外衣,当预付卡变成“资金池”,当情感绑架替代专业服务,消费者正在为行业失序付出健康与财产的双重代价。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个案查处,而需通过立法明确非法行医与消费欺诈的刑事边界,通过技术手段实现预付卡资金全流程监管,通过公众教育破除“排毒养生”的伪科学迷思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美容经济回归“服务本位”,而非沦为资本收割的狂欢场。